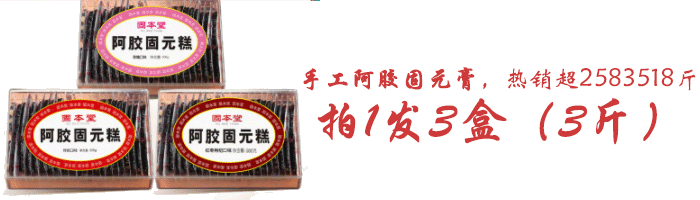很多年以前,我还很年轻。年轻到除了上课、下课,熬夜做习题应付考试,生活里就只有风花雪月,我根本不知道这世界上还有一种东西叫做“阿胶”。
“阿胶”一下子被送入我的生活,因为我的眼睛突然看不见了。
没有任何先兆,就是在那个一觉醒来的清早,突然发现自己无论怎样用力睁开眼睛,整个世界还是一片灰濛濛。不是漆黑,是浓重的,化不开的灰濛濛,因为我还有光感,还知道天黑天亮,灯开灯灭。
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每天被各科不同的医生护士们推送着做各种检查,我一直很安静,很配合。并不是心理有多强大,只是懵懂。事情发生得太突然,突然到不像是真的,我根本反应不过来,连害怕都来不及。
可怜的是家里众人,他们并非如我一般迟钝。那时祖母和外公、外婆都健在,在儿孙辈中他们向来偏疼我一些,从不掩饰。眼看着两个月前好端端过完暑假,好端端回学校去念书的我,突然被送回来,躺在医院里双目失明,他们受到的惊吓和刺激绝不止一点点。
“要加强营养,”他们说。实际上,这也是所有焦虑的长辈们能为生病的孩子所做的唯一一件事情了吧。我的家乡在亚热带的南方,那里的人们坚信补充营养最好的方式就是喝汤。我听见一阵悉悉索索的,折叠牛皮纸的声音——失明的人,耳朵变得特别灵敏——外婆将什么东西递给母亲,说:“你爸说,每天做汤都给她放一点儿。”
于是我开始每天喝各种汤。乌骨鸡蘑菇汤,枸杞叶猪肝汤,甲鱼丝瓜汤……据说有养肝明目功效的每一碗汤里,都有这样东西。
两周之后,我逐渐复明。虽然视力再也不能恢复到从前的水平,但总算是又能看见了。出院以后返回学校上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母亲还要我每天喝各种汤。某天偶然看见母亲存在厨房的一个牛皮纸包,直觉地认为这就是外婆在医院里给母亲的那一个。好奇地打开来,只见里面还剩下半块棕黑色的小硬片,平滑的表面有红色的“阿胶”二字。拿起来迎着光,断面有些半透明。
“是上等的山东阿胶,”母亲走过来说。“你外公交代,每天要给你放半块在汤里吃。”
阿胶。从此我知道了这味药材,知道了最好的阿胶产地在山东。后来还知道阿胶属于比较名贵的中药材。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当年,家里的经济条件并不宽裕,而我每天吃半块最好的阿胶,持续了那么长的一段时间,都是我外公给的。
我外公个子不高,也清瘦,为人老实厚道,不善言辞。我印象中,他不大和我说话,甚至从来没有抱过我。我从小平日里跟着祖父母就学,我的幼儿园在外公上下班的必经之路上。我经常站在幼儿园门口,等他骑着自行车经过,对他喊:“公公!礼拜天记得过来接我!”
他只是骑在车上点点头,叮嘱我要乖乖听话,从未在我面前停下来过。不过到了礼拜天,外公就骑着自行车来接我了,接我去外婆家。外公自行车的车头上,总是挂着一个人造革的半旧黑公文包,包里总有一个小闹钟。小的时候,我总是想不明白,不是有样东西叫手表吗,小巧精致的手表不是更方便吗,为什么外公要天天带着这个笨拙难看的闹钟看时间呢?!
回到外婆家,绝大多数时间我是和外婆在一起的。陪着外婆下菜地,摘了一大盆枸杞叶回来,见外公坐在客厅的椅子上看报纸,手边放着一个苍蝇拍。南方盛夏的苍蝇真多,飞进屋里一个,外公就拿起苍蝇拍收拾一个。后来学到书里有“眼疾手快”这个词,觉得就是我外公拍苍蝇的姿势,一拍一个准儿,鲜少落空。和外婆一起去看完一场电影回来,外公还是坐在客厅的椅子上看报纸,只是脚边换了火盆。亮蓝色的火苗在黑色的木炭缝隙间窜动,煨着深棕色的一罐葱根老姜茶。见我进了门,外公抬起头来吩咐:“外面冷,过来喝了,祛祛寒气。”他知道我自幼不吃甜食,往往接着要解释一下:“茶里放的是盐,不是糖。”
从我祖母家到外婆家,是公共汽车三站路的距离。没几年我自己可以搭车往返,不用外公来接送了,可他终归不放心。他知道我在这头上车有祖母送,便等在下车的那一头接。那年头也没有手机,他就估摸着差不多的时间,站在二路车的站牌下一直等。有一阵子他除了上班,还要到附近一家中专去教课,特别忙。要是某个礼拜天顾不上接我,他也会交代姨母或舅舅到那个站牌下去等。直到我都已经上高中了,不论刮风下雨或大毒日头底下,每次我一下公共汽车,也还总有人站在那里接我。
我外公解放前从会计学校毕业,是一位资深的老会计师,我却没有遗传到一星半点他对数字的敏感度。可是这并不妨碍他宠爱我。对于他来说,只要我是我,就好了。他对我完全没有要求,他对我的爱也没有任何附加的条件。每年春节他给孙辈发红包,我这一份肯定是金额最大的。当全国人民都才刚刚开始将厚重的棉袄换成轻薄的羽绒衣,我就有了一件纯白色镶大红边,出口转内销的漂亮羽绒衣,因为外公知道我特别怕冷。每当我在外面闯了祸,无论是谁——哪怕是母亲——去向他告状,他都一概否决,在他眼里,我简直完美到毫无瑕疵,他拒绝任何人判定我有瑕疵。
而我渐渐长大,渐渐离开他越来越远,终于远到隔着整整一个太平洋。我在温带的美国北方给他写信,告诉他满山的叶子红遍了,或者天又下大雪了,或者,春暖花开了,告诉他身在异国他乡的我,没有生病,没有被什么人欺负,让他放心。这是后来长大成人的我,能为他做的唯一的一件事。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某个夏天家乡连遭暴雨,大水涨到外婆家的客厅,家俱什物大半被淹,剩下的后来也多数霉坏,而我写给外公的信,我寄给他的照片,尽数完好无损。
1995年,我被当时工作的公司送到广州参加春季广交会,会后回家探亲,外公已经退休了。那一次回去真的搅得家里上上下下如一锅沸水,因为不仅我这个人回来了,还在短短的探亲期间发现有了身孕。我腹中的胎儿,是家里的头一个第四代。我返美的行李箱中,于是被家里人塞满了各种大大小小的婴儿衣物、用品,外公先给我的是一床羽绒被,他还是惦记着我怕冷。
到我临走那天,给我送行的亲友挤满了一屋,外公再递给我一个小铁盒,说:“带着吧,记得吃。”那是一个黑色底起大红印花边,密封的小铁盒,盒面上最大的两个烫金的大字:“阿胶”。
外婆和姨母、舅母们,要叮嘱我的话说也说不完。可我必须要走,她们只得跟出门来送,送到不能再送,才停下来。我坐进车里摇下车窗,回头向他们招手,看见我外公默默站在所有人的最后面。
那天,他和往常一样,穿着一件白色的确良短袖衬衫。
再回到美国,我继续给他写信。告诉他,我在孕期里特别能吃,整个人胖了二十多斤,挺着个大肚子来来去去,周围的朋友们都叫我“航空母舰”;告诉他我在大雪纷飞的圣诞夜顺利产下了一个大胖丫头;告诉他我身边虽然没有亲人,但朋友们都特别好,尤其是比我年长的大姐阿姨们,排着队照料我和婴儿,轮流天天炖汤,那一盒阿胶已经被我吃完了……
等小丫头满了周岁,送她去上了幼儿园,我自己开始读硕士学位。外公并不经常给我回信,隐约听说他的身体不大好。我外公是心脏病的老患者,伴有严重的哮喘,我很小就知道。我出国之后,但凡他犯病住院,家里人从来不会直接告诉我,而我,也根本不敢主动去追问详情。
学校的功课繁重,我坚持了大半年之后还是生病了。家里人得到消息,在太平洋的那一头急得不得了,偏偏母亲和婆母轮番申请到美国来的探亲签证,都不顺利。无奈之下,家里让我把当时未满两岁的小丫头送回国。我自己脱不开身,最后是托朋友把孩子带回去的。外公见到她,只连声说,长得像我,是小时候的我又回去了。——而他自己,已经重病垂危,住进了医院。
等我病好了,拿到硕士学位之后再回国,只剩下去给我外公扫墓的机会了。那次探亲期满带上小丫头返回美国,为我们母女送行的亲友在机场候机厅里站了一大群。我在过海关之前回身向他们招手,在他们当中,再也搜寻不到我的老外公,那个我熟悉的,个头不高,时常穿着一件白色短袖的确良衬衫的,清瘦的身影。
可我随身的行李中,还有一盒阿胶,是外婆交给我的。也是密封的铁皮盒子,和上回的大小差不多,只是外观显得更加精致。外婆说,外公当时听说我生了病,特地给我留下的。可是,那个时候他自己也经缠绵病榻了啊,怎么还要留给我?!外婆说,带走吧,你自己好好的,公公婆婆就放心了。
如今,外公当年说长得很像我那个小丫头,已经大学毕业了。她每年冬天用着的羽绒被,还是我怀着她的时候,外公让我带回美国的那一床。十几年间我读了更多的书,又添了一个小丫头,再走上大学讲台教书,我们搬过两次家。厨房壁柜的一角,那两个铁皮的阿胶盒子总在那里,一个已经空了,还有一个依然密封着,我从未打开过。
也曾经有颇知几分医道的朋友看见这两个盒子,问过我,这么好的东西怎么白放着不吃呢?还热心地教我应该如何如何吃,我才知道原来阿胶还有各种不同的,或许比放进汤里更好的吃法。不过也没想过要把密封着的那一盒打开来吃掉,总觉得自己更需要的是,每次拿起那个盒子,能感觉到它满满当当的重量。有了那点重量,便仿佛所有的时间都未过去,只要我搭上二路公共汽车,过三站路一下来便能看见我外公,依然静默地站在那里,等我。
有一回小表妹到美国来看我,带来一大袋阿胶糕。用阿胶混着核桃、芝麻做成,加了蜂蜜或糖,一小块一小块单独包装。打开来吃着,很想再写封信告诉我外公,这种阿胶糕是甜的,但不是那种让我觉得腻烦的甜,又方便又好吃啊,我很喜欢——还有,我现在很少生病了。
纽约上州,我家里厨房的壁柜中一直有两个叠放着的阿胶铁皮盒子,一个已经空了,一个还是满的,静默在固定的位置上,我每次一打开壁柜,就能看见。
**获第三届东阿阿胶“明月心·中秋情”征文大赛二等奖
本文由“文字之光”荐文官瑾字翁白居难推荐
本文由“文字之光社区”助力。
【文字之光】是已立项注册,自2020年元旦始启用。
【文字之光】是由文字之光社区居民秉持 “为好文找读者、为读者找好文”的价值理念而设立的专题,专题目前不接受投稿。
广大优秀作者可以投稿到它的优选专题【金色梧桐】中,编委会从中选出优质文收录到【文字之光】,并从中精选出最优质文加以推广。
我们期待你的优雅亮相!你若能甩出掷地有声、灵动有趣的文字,我们定会用足够的真诚与你的文字共舞,让优质的文字发出耀眼的光芒。

见证优秀 共同成长
找到我们有两种方式:
01 在微信群中搜索文字之光
02 发私信给文字之光主编韩涵微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