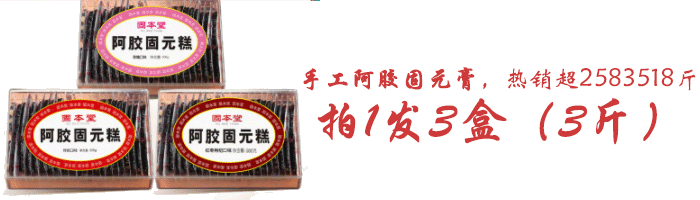原标题:刘亮程:1999——一张驴皮|天涯·作家立场
天涯微信号:tyzz1996
天有际,思无涯。
投稿邮箱:tianyazazhi@126.com
刘亮程历时5年创作完成的长篇小说《捎话》,秉承和延续了其自《一个人的村庄》开始就为读者所熟知的“万物有灵”创作观。在语言上,贯穿着他追求的玄学趣味,呈现出情感与哲学融合的动人特质,是他脱离“散文家”身份的再一次超越。
本文可谓是《捎话》的创作背景,然而并不拘泥于《捎话》的创作,而是展现了一个“散文版”《捎话》的现实世界,作者以他特有的语言风格,讲述了与驴、与新疆、与于阗国和喀喇汗王朝那些西域千年历史的关系。今天推送,以飨读者。
点击上图,一键购买
1999:一张驴皮
刘亮程
气味
火车驶离乌鲁木齐时天色已暗,我坐在一车厢说着维吾尔语、蒙古语和汉语河南话、甘肃话、四川话的嘈杂乘客中间,不同语言散发的气味混合在一起,闭上眼睛我也能闻出哪个气味是哪种语言发出的。后排那群四川人大声说着去年在南疆摘棉花遇到的各种事情时,空气中满是他们嘴里的大肉炒辣子味儿。他们或许就在火车站旁的川味餐馆里吃的晚饭。上车前我在那家川菜馆挨着的清真饭馆吃拌面时,辣子炒肉的味道和嘈杂的四川话从隔壁传过来。坐我对面的三个维吾尔族男人一定闻出我身上和他们一样的羊肉拌面味道,我眯着眼睛,透过一丝眼缝看车厢里的人。
前排的四个蒙古族男人,把拎来的两瓶子白酒和一包花生米堆放在餐桌上。我在这辆火车上碰到过喝酒的蒙古族人,他们喝高度白酒,低沉地说着蒙古语。若是在草原上,他们悠扬辽阔的歌声早已经唱起来了。火车上的环境让他们有点压抑。他们一直喝到半夜,把一车厢的其他语言都喝睡着了,火车到达库尔勒,他们摇晃着下车。
对面的三个维吾尔族男子要了六瓶啤酒,用牙咬开,倒在纸杯里,一人一杯转着喝。其中一个把啤酒杯朝我举了举,对我说了句维吾尔语,我对他笑笑,摇摇头,没吭声。他把我当自己的同族了。我跟他一样留着小胡子,前额的头发压住眉毛,因为清瘦而显得眼窝深陷。这是二十年前的我,眼神忧郁,看上去既像维吾尔族,又像哈萨克族和蒙古族。
我的斜对面坐着两个甘肃人,也是去南疆摘棉花的,棉花在他们说的甘肃话里,厚厚绵绵的,像是落了一层土,这是我老家的语言。他们中的一个斜眼看着我,他肯定一眼认出我是吃洋芋长大的甘肃人。我出生的前一年,父亲携家带口从甘肃金塔逃荒到新疆,在北疆沙漠边一个小村庄落脚,我在那里出生长大。我的长相中有我父亲的甘肃人相貌,又有我在西北风中长成的新疆人模样。可是,刚才对面的男人跟我说维吾尔语时,我微笑摇头的样子,可能让那个甘肃人认为自己看错了。
我不说话,他们就不知道我是谁。
做梦
火车过天山时我睡着了,我从北疆一路昏睡到南疆。醒来时火车已过库车站,对面三个男人不见了,换成两个戴头巾的年轻妇女。我赶紧摸衣服口袋,看行李架上的包。这个下意识的动作让我自己不好意思起来。邻座的人都换了,没一个眼熟的,那两个甘肃人也不见了,好像这一觉把我睡到了另一个世界。
“你做梦了。”戴黑头巾的女子用半生不熟的汉语说。
我突然想起在梦里见过这个黑头巾女子,在我没有完全闭上的一只眼睛里,一个黑头巾女子坐在对面,用她黑黑的大眼睛看我。之前我一直眯着眼睛,半醒半睡地听三个男人用维吾尔语说话,其实只有两个人在说,正对着我的那个好像不爱说话,但他一直盯着我看。这个跟我一样上嘴唇边蓄着胡子的男人,可能在我沉睡后说出的梦话中,惊讶地听出来我是一个汉人。
“你说了大半夜梦话,吵得我们都没睡觉。”女子说。
“你还像驴一样大叫,把睡着的人都叫醒了。”
车窗外一轮大月亮挂在半空,火车在穿越南疆大地。夜色里一晃而过的低矮村庄,灰色的,零星亮着的几扇窗户,像谁遗忘在深夜的家。早年我常梦见自己被人追赶,在灰暗的村巷里惊慌逃跑,整个村子没有一扇亮着的窗户,所有院门紧锁,我恐惧地跑出村子,荒野上没有月亮和星星,追我的人越来越近,仓惶中我发现自己突然长出蹄子,变成一头驴放趟子跑起来。又好像我脱身站在后面,看见一头驴替我逃跑,追我的人在拼命追驴,眼看要追上了,我一着急发出一长串驴鸣。
“昂叽昂叽昂叽。”
母亲一听见我在梦里发出驴叫声就赶紧喊醒我。

作者拍摄的南疆风情。
我们家没养过驴,但邻居家有。村里家家养驴。我从小喜欢学驴叫。我能跟驴说话。我躲在草垛或土墙后面学公驴叫,能把母驴唤过来。我学母驴叫能引来一群公驴。我母亲怕我跟驴走得太近才不养驴,她最担心我长大后变成一个驴里驴气的人。
我不好意思地向黑头巾女子笑了笑,她的微笑从头巾后面浮出来,我看不清她的面容,我想那一定是一张美丽的隔在梦中的脸。
捎话
火车站广场上乱糟糟的,出租车和抢客的黑车混在一起。稍远的马路边停着一长溜毛驴车。那时毛驴在喀什城郊还有各种各样的活路,通往乡下和偏僻街巷的路还是驴和驴车的。我本来想找一辆汉族司机的车,转一圈没找到。前年我到喀什还打到一辆汉族司机开的出租车,他用一口流利的维吾尔语问我去哪。
拉我的维吾尔族司机也把我当成了本族人,他用维吾尔语问我去哪。
“艾提尕尔清真寺。”我用汉语回答。他扭头看了我一眼。
三天前,喀什文管所的老孙捎话来,说艾提尕尔清真寺边的买买提捎话给他,让他跟我说,有好东西了,赶紧去。买买提是老孙介绍给我认识的。他在清真寺旁开了家古董店,专收农民送来的老东西,又转手卖出。老孙是我在喀什购买老东西的向导,他跟喀什的古董摊贩都有联系,每当他带我去一个店,就鼓动我买他认为有价值的东西。
“这些东西错过就再没有了。”老孙说。
那时喀什老城的老东西多得没人要,在巴扎上,随处能看见摆卖的老古董。一次我在卖瓜果蔬菜的巴扎上,见一疙瘩锈在一起的铜钱跟土豆摆在一起,问了土豆的价钱,又问铜钱多少钱卖。农民说,挖土豆时一起刨出来的,要的话,跟土豆一个价。
长路
那些年我经常来喀什,早先坐班车,挤在一车厢说维吾尔语的人中间,遇到刮风时,昏天暗地,仿佛永远没有白天,我和他们一起睡着醒来。我醒来时眯着眼睛听他们大声说笑,我听不懂那些笑话的内容,但知道一定很可笑,也跟着一起笑。
有时一车人都在沉默,窗外辽阔单调的沙漠在沉默,天山光秃秃地立在右边,天上灰蒙蒙飘着尘土,这样的时间仿佛再生长不出一句笑话,车厢里也是呛人的浮土,土往人睫毛上落,把眼睛压得闭住。
突然,后排有人扯开嗓子唱起来,声音沙哑高亢,瞬间胀满车厢,又在车窗外面的荒野中回响。我听不懂歌词,但能听懂声音,那是沙漠里忧伤的歌,歌者的嗓音里弥漫着尘世的沙子。
睡着的人眨眨眼睛,在醒与睡间徘徊的当儿,歌声戛然停住。他只唱出孤单的两句,像是忘了词儿,我等他想起来再唱下去,等了不知多久,也许客车已经行驶了几十公里,扭头见那唱歌的老者已然昏昏睡去。
半车厢人睡着了,路还远呢,村庄过去是茫茫沙漠。客车不时地在一处沙丘旁或红柳丛边停下,男女左右分开,在荒野中方便。那时从乌鲁木齐到喀什,客车要走两天一夜,两个司机轮流开。乘客也轮流睡觉,同一时间,总有人和其他人睡不到一起,别人睡着时他眼睁睁望着窗外,大家都醒来时他睡了。也有人白天把觉睡光了,晚上睁大眼睛,看别人睡觉。
我强忍瞌睡,等到满车厢的鼾声响起,维吾尔语的梦话前一句后一句地说起来,语言携带的气味浓郁起来,这时候,我才迷迷糊糊睡着。
我一睡着就暴露了自己。一车人中就我一个用汉语说梦话。我平时说话轻言慢语,但梦中说话声音大。我知道当我突然说出汉语的梦话时,醒着的人会扭头看我。
喀什
我喜欢乘车离开乌鲁木齐往喀什走的感觉,仿佛走向一个深不见底的过去。
那时的喀什,在我的感觉里确实是一个大半截身子还没有走到现代的城市,它满街的汽车轱辘和人腿加起来,也没有毛驴的腿多。喀什被毛驴驮着运转,街上都是驴和驴车。我一直认为毛驴是往回走的动物,它们对去一个新地方没有兴趣,这个赶驴人都知道。他们经常遇到的事情就是,赶驴车去沙漠戈壁打柴,人在车上丢个盹,驴就调转头往回走了。我感觉当地人对未来的态度也差不多,尤其是男人们,喜欢背着手走路,你看他们脸朝前走,两只手却背在身后,操劳着过去的事情。

作者拍摄的南疆风情。
我的两只手也在倒腾过去的事情。我喜欢文物,他们管文物叫老东西。一次我到喀什英吉沙一个贩子家,我问,家里有老东西吗?那男人看我一眼,转身带我到屋后的葡萄架下,指着坐在荫凉处打盹的白胡子老头,说,这是我们家的老东西。
那男人跟我开过玩笑后,手伸到一堆干草下面,掏出几个坛坛罐罐来。
喀什确实是一个属于过去的地方,它的街道、巴扎、做手工的匠人和拉车的毛驴,都在离我很远的时间里。我知道回到过去的路,在世间所有道路中,我最熟悉的一条就是回去的路。人们一路留下的老东西上有时间的印记。
我一直盯着喀什的那个时间在看,它像沉在水底的一枚银币,我等待它浮上来。我看跟它有关的所有文字,看出土的那个时期的文物,我不知道想看见什么。
五块
出租车在艾提尕尔广场停住,问多少钱,司机伸出一个巴掌,我会意地笑笑,递去五块钱。上一次我从汽车站坐驴车过来,赶驴的老者也伸出一个巴掌,他望着竖立在广场上“毛主席挥手指方向”的高大塑像说:“五块,毛主席说的。”
这座毛主席像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塑的,当时不少县市的中心都塑有一尊“毛主席挥手指方向”的高大塑像,喀什的雕像也成为这座老城最显著的地标。这尊毛主席像经过塔里木盆地几十年的风吹日晒,也越来越像喀什人了。

艾提尕尔广场上的毛主席像。网图。
我在玉器店也见过雕刻的毛主席头像,怎么看都像有点当地人的长相。我想,这肯定是当地玉雕师傅的手艺。有一点当地人味道的毛主席像,或许更加让人感觉到亲切。
那些年,毛主席伸向空中的一只手,给喀什所有东西定了价。拌面、抓饭、帽子、套鞋、皮带和一公斤葡萄干等等,都是五块钱。“五块,毛主席说的。”——这句话成了全喀什的流行语,那些东西的价格过了这么多年也不变。
驴皮
老孙已经等在文物店里,店主买买提从塞满了旧铜器的柜台下抽出一卷压扁的皮子,皮子毛面朝里卷又从两头对折过来,像一个包裹,一看就有些年头了。
买买提打开对折过来的皮子,嘴里不停地说着维吾尔语。老孙翻译说,买买提说他刚收来的时候,皮子又干又脆,不敢动,喷了水,阴了几天才柔软了。
接着皮子慢慢摊开,皮面是光的,剔了毛,但边角处还留有一些黑毛。
“是张驴皮。”我说。
我原以为皮子里裹着什么贵重东西,直到一张完整的驴皮摊开在柜台上时,却没看见任何东西。
“这里。”买买提指着已经发黑的皮面让我看。我凑过去,果然看见皮子上模糊的文字。
“是回鹘文。”老孙说。
我忍住怦怦的心跳,却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在皮面上扫了几眼,密密麻麻的回鹘文写满一张驴皮。
老孙和买买提都知道我喜欢喀喇汗王朝时期的老东西,尤其对回鹘文书之类的东西见了就买。
我努力把心放平静,抬头问老孙:“啥内容?”
“应该是佛经。”老孙说。老孙和我一样,只能认出回鹘文字的形,并不懂啥意思。
“怎么样?”过了好一会儿,老孙问我。
“谈谈价再说吧。”我心不在焉地看旁边柜台上的东西,脑子里浮现的却是写满整张驴皮的回鹘文佛经。
买买提只会说一些简单的汉语,老孙的维吾尔语说得很溜。我故意离开点,听他们俩用维吾尔语讨价还价,我假装听不懂,其实我确实听不大懂,只听他们说一些钱的数字。
买买提说三千。
老孙说太贵。
买买提说三千卖了你有五百的排档子(好处)。
我摸摸口袋,只有一千块钱。
我正盘算着,老孙叫我,说:“买买提要五千块,我降到了三千块,你看怎么样。这个东西确实罕见。”
我说:“现在出土的回鹘文佛经多,不稀罕。”我让老孙给买买提翻译,说写在驴皮上的佛经不好,死驴皮是最不干净的东西,留在店里也不好。
没等老孙翻译,买买提说:“你给个价,多少钱买。”买买提听懂我说的汉话了。
我把口袋里的一千块钱全掏出来摊在手里。
“我就带了一千块钱。”我把四个口袋全都底朝上翻出来让他看。
“我得留下三百块住宿和买回去的火车票,剩下的七百块钱全给你,卖我就拿走,不卖就算了。”
买买提把摊开的驴皮又卷起来。“一个毛驴子还七百块呢。”买买提嘟囔着。
老孙忙用维吾尔语跟买买提讨价。老孙说:“你看,刘老师是我的老朋友,也是你的老买家,这些年买过你不少东西了,这个死驴皮嘛就便宜卖给他吧,下次他钱带多的时候,再贵一点卖给他别的东西。”
买买提说:“看在你的面子,我最低一千块钱给。你的排档子嘛就没有了。”
老孙说:“这个样子吧,我让他再加一百块,八百块钱成交行了。排档子的事以后再说。”
买买提无奈地点了点头,用半生不熟的汉语跟我说:“看在老孙的面子,八百块,一毛都不少。”
老孙也说:“你看这样吧,这个东西我也是第一次见,让别人买走就可惜了。你给他八百块吧,今晚你就住我们单位宿舍,住宿钱给你省下。你看咋样?”
我赶紧说谢谢谢谢,从手里的钱中抽出两百块,其余的全递给买买提。
巷子
老孙说单位有事先走了,我没让他陪我,我要去的地方他不知道。其实我也不知道要去哪。我背一卷干驴皮,往艾提尕尔广场后面的巷子里走,走一截抬头看看清真寺上的弯月,有一段看不见了,我就往更远的巷子走,直到又仰头看见那枚弯月。这时我脑子里浮现的却是一千年前的一座佛寺,我没想过要来找到它,就像从来不想认识我收集的文书上那些回鹘文、于阗文和龟兹文。我只是长久地琢磨和喜欢着它们不被我认识的样子。

汉字与回鶻文•吐鲁番 10世纪 木头沟,网图。
巷子里满是往来的驴和驴车,我背一卷干枯驴皮走在其中,感觉驴都在斜眼看我。我能想到驴看见一个背着驴皮的人是什么感觉。
不时有驴鸣响起。我仔细辨认驴的叫声和音节,跟我小时候在北疆村庄听见的驴叫一模一样。驴不会随着人的口音而改变叫声,狗却会。在我们北疆村庄,河南庄子的狗会叫出拖长音的河南腔来。甘肃人村庄的狗叫声则仓促厚实,能听出甘肃话的味道。我住的村子河南人和甘肃人各一半,听叫声我就知道哪条狗是甘肃人家的,哪条狗是河南人家的。一次在乌鲁木齐跟朋友喝酒,他们都在说段子逗笑,我把这个早年的发现说给大家听,还学了河南腔和甘肃腔的狗叫,他们都以为我在讲笑话。
我对声音有特别的敏感,早年我学鸟叫,能把树上的鸟儿叫到地上来。我学乌鸦的叫声尤其像,村里常有乌鸦集结,有老人的人家都害怕乌鸦在自己家的树上叫,说不吉利。我却喜欢乌鸦,我学它啊啊的叫喊时,感觉自己是一个心在天上的高傲诗人。
我学得最像的是驴叫,如果我在这个墙角学公驴叫,一定能把那头拉车的年轻母驴叫过来,但我忍住没叫。
回来时我坐了辆带凉棚的毛驴车,赶车的老人对我笑笑,我递了两块钱给他,在巷子里看不见毛主席像,也不用给一巴掌钱。那头驴走几步,扭头看我,也许在看我抱在怀里的干驴皮。
翻译
晚上在老孙单位宿舍,我小心摊开驴皮,用放大镜逐字逐句地看,我熟悉那些回鹘文,这些年我收集了不少回鹘文古文书,但我从未试图去解读。我喜欢长久地看那些我不认识的古老文字,对其保持着难言的陌生与好奇。
老孙给我找的回鹘文学者来了,他叫库尔班,大胡子,看样子有六十多岁,汉语说得很好。老孙说库尔班老师能读懂这里出土的所有古老文字。
库尔班拿着我的放大镜看了好久,说这是由于阗文转译的回鹘文《心经》。他指着驴皮脖子左下角的最后一行字说:“这里注明是于阗王新寺马主持捎给疏勒桃花寺买生主持的佛经。”
我的血再一次涌到头顶。我在多年的收集阅读中早已熟知这两个寺院的名字。当库尔班说出于阗王新寺和喀什桃花寺时,我就像在很远处听到有人说起我家乡的名字。
送走他们后我又匍匐在驴皮上,拿放大镜仔细辨认,我拿熟记于心的汉语《心经》一句句地对着回鹘文读,当对照到“究竟涅槃,三世诸佛”时,我猜想回鹘文中“佛”是哪个字,又担心我认识了它。我着迷的是字不被认出时的样子。
我的注意力落在边缘的皮毛上。
这张驴皮剥得很完整,从蹄子到脖子、头,整头驴的形状完美无缺,尤其令我好奇的是,它萎缩的尾巴根部,完好地保留了毛驴后阴部分,让我一眼看出这是一张小母驴的皮子。
皮子从驴脖子靠耳根处整齐割开,驴头部的毛没有剃去,能清晰地看出一头完整的驴脸。
应该是一张于阗小黑母驴的脸。
我观察过于阗驴和喀什驴,两者的差别是于阗驴毛色黑,喀什驴偏灰,但驴叫声没有差别。
我猜想这些文字应该是驴活着时刺在驴皮上的,这头小母驴身负一部《心经》,从于阗王新寺,走到喀什桃花寺。这期间喀喇汗和于阗的拉锯战打得正酣。这头小母驴一路经历了什么?我怎样才能知道它所历经的所有故事?
倔强
从喀什回到乌鲁木齐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精力集中在这张驴皮上,我把之前收集的于阗、喀喇汗王朝时期的文书和器物摆在铺开的驴皮周围,每日把玩琢磨,我想象这头留下一张皮子的小黑母驴,一定看见或者驮载过这些东西。那时毛驴是主要的驮运工具,人驴形影不离,人拿过的,驴都驮过。
我想着这头小黑母驴时,时常嗓子痒痒的想放声鸣叫。我脖子伸直,脸朝上,喉管一鼓一鼓,却从没有发出过一丝声音。
有一天,我突然决定开车去和田,再到喀什,沿着这头驴走过的地方走一遍。那也是一千年前于阗国和喀喇汗王朝间拉锯交战的战场,至今留有大量麻扎和佛寺遗址。我在手绘地图上标出那时候从于阗到喀什的佛寺和麻扎的名字及具体位置,它们连接起一条一千年前的路。
可是,这一行程在半路上的库车终止了。
作者拍摄的万驴大巴扎。
我被库车老城满街满巷的驴和驴车留住。那时的库车县四十万人,有四万头驴,四万辆驴车。每个周末龟兹河滩上的万驴大巴扎让我流连忘返,仿佛全世界的驴和驴车在那里聚集。我在巴扎上听驴叫,有时偷偷地跟驴一起叫。
巴扎上全是驴和人的嘈杂声,我在驴堆里闲逛,摸摸这个的脖子,拍拍那头的屁股,看没人注意,蹲下身,喊出一声驴鸣。旁边的驴立刻跟着叫起来。我小时候跟驴学的叫功,随着年壮喉粗显得愈加苍劲逼真。当我和驴一起大叫时,没有人听出满河滩的驴叫中有一声是人的,我也不觉得我是一个人在叫,只感到我和驴是一伙的。我昂起头,伸直脖子,扯开嗓门,我听见我在驴世界里的声音,比我在人间的更大更响亮。
作者拍摄的万驴大巴扎。
我在库车的数年间,目睹驴车被电动三轮车替代,“昂叽昂叽”的驴叫变成“突突突”的机器声,我经历了毛驴从极盛到几乎灭绝的全过程。那是驴的末世,是驴和人在这个世界的最后交集。
我憋了一股子倔强的驴脾气,写成《凿空》这部书。
现在,人们只有在我的书中才能找到那么多的驴,听到那么昂扬的连天接地的驴叫了。
我在库车过足了一个人的驴瘾。
我以为我把驴的事情交待完了,以后我再不会写到驴,这个世界跟驴没关系了,所有路上不会有驴蹄印,田野里不会有驴叫,连天堂里也不会有往来的驴车。
可是,我的梦里还有一头驴活着。
作者拍摄的万驴大巴扎。
一个夜晚我又梦见自己被追赶,我在恐惧中拼命逃跑,眼看被追上,我看见自己四蹄着地,放趟子奔跑起来,脚下是熟悉的荒野沙漠。
这一次,我清楚地看到梦中替我奔跑的那头驴的脸,白眼圈,黑眼睛,眯一个缝看我。在我早年的无数个梦中,我都只看见它奔跑的蹄子,仿佛我爬在它背上,又仿佛脱身在别处,我把恐惧和被追赶的命运扔给了它,却从来没有看见它的模样。
醒来我突然想起那张驴皮上的脸,我取下放在书架顶上好久没动的那张驴皮,小心展开,我惊讶地看见一张和梦中那头驴一模一样的脸——一张小黑母驴的脸。
我突然又有了写驴的冲动,我写过库车的万驴巴扎,写过河滩大巴扎上的万驴齐鸣。
这一次,我要写一头小黑母驴,我给它取名叫谢,我听见它的叫声了。我也听懂它在叫什么。
我写的这部书叫《捎话》。
刘亮程,作家,现居乌鲁木齐。主要著作有《一个人的村庄》《捎话》等。
相关链接:
《天涯》2023年第1期简介及目录
刘亮程:月亮在叫
刘亮程:把地上的事往天上聊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责任编辑: